張正離開《四方報》 你不知道的搞砸內幕
以下以第一人稱,來聽聽張正在媒體之路的搞砸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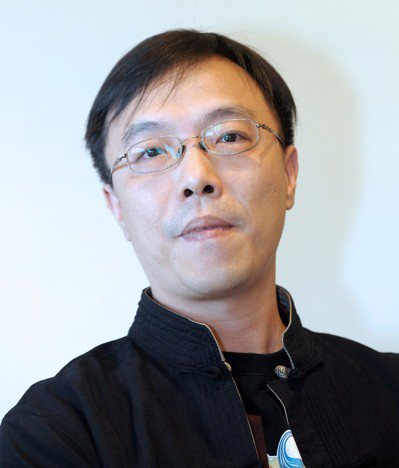
我大學念政治大學,不是新聞系,但是就覺得自己好像還可以寫點東西。那時我每次騎摩托車去政大,會經過世新大學,看到世新校門口就寫「台灣立報」。那時候獨立不是可以明目張膽講的事情,我心想:「哇,世新那麼屌,把『獨立』就直接畫在那個牆!」不過後來我去《立報》工作才知道它根本不是要搞獨立。
《立報》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多元公平乾淨的社會,對於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還滿好的,我們都相信要做這樣的事情。這個社會對記者或是媒體工作者都有一些想像,像是寫一些正義相關的、打抱不平的。我剛開始當記者的時候,我的親戚都會透過我媽打電話跟我講:「我們家這邊路燈壞了,趕快來報導一下。」我想說這又不是我的線,而且路燈壞了到底要找誰我其實也不知道啦。(笑)
我們要做一個「平衡所有媒體」的媒體
《立報》專門做社會運動、教育、勞工、老弱殘疾,就是所有跟你們不相干的議題。不啊,還有同志。當年同志題目在台灣很冷門,我們有一個版做同志、做性別,曾經被高層干預:「你們幹嘛一直做同性戀,沒有東西可以做了嗎?」可是我們老闆成露茜(已過世)還滿好的,她說我們就做我們該做的事:我們要做一個平衡所有媒體的媒體。

就是《立報》去平衡所有的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右派媒體,只有我們是左派媒體。那時候台灣的媒體那麼多,槍林彈雨,我們那麼小一個報社,其實沒用的。我們出版量也少,也沒有印幾份,然後就--好,所以就失敗!
《立報》這樣一個經營成本不高的單位、資金不多的單位,裡面的人也沒有很厲害,像我這種半路出家去做的,也不太可能真的對抗其他的大媒體。我記得我進去不到一年就變成政治組組長。政治組其實是那個時候媒體最大的組,那我才進去一年而已,人家連資深記者都算不上。
因為政治組只有我一個記者,我去跑立法院,就是我愛跑哪一間就跑哪一間,每一間都可以跑。跟那種大報比起來,一個跑立法院的記者群7、8個,跟我們整間報社的記者人數一樣多,所以其實根本不太可能去抗衡。不過這個理想還是對的。
2006年,我們另外創立了《四方報》,那是一份給台灣外籍人士看的報紙,不是英文的,英文太好的我們都很討厭他,不是嗎?(笑)我們是為印尼人、泰國人、菲律賓人、柬埔寨人這些人辦的,希望可以讓他們在台灣社會過得更好一點。
成露茜用了一個巴西解放教育學家的說法:你要真的翻轉他們的處境,要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講話,有能力可以講話,讓他們在台灣這個社會可以真的發生發出聲音,可以真的得到資訊。

那年《四方報》辦了2種語言:越南文和泰文。越南文四方報基本上當時算成功,那泰文報是失敗的,閱讀量低。我後來又重新辦了泰文報,因為台灣還是有泰國勞工,我們還是撐下去,還是繼續辦,可是還是很辛苦,願意看的泰國朋友少。我後來的解讀是,男生真的比較不愛閱讀,因為泰國來的都是男生。(笑)
當他們接下報紙說謝謝,繼續滑手機,我就知道那個時代過去了

其實我是「文盲總編輯」,我不太懂越南文。我在越南待過4個月,去學越南文,在那邊講話都講越南文或英文,我最常看的電視節目就是足球,因為足球不用講話,就是踢來踢去。外籍移工寫了很多信來要放在四方報上,透過此發聲、表示意見。
意見好壞不重要,就是有個地方能講。我們甚至還收過訃聞。我雖然看不懂,但是我們報社有翻譯,那段期間讓我對在台灣的東南亞人有更清楚的認識,因為他們在《四方報》不斷的表達自己、發表意見。
後來當然失敗了,《四方報》已經停刊了。為什麼失敗呢?這要怪祖克柏,因為他發明了臉書。《四方報》被稱作外籍勞工的紙上臉書,因為他們在台灣只能透過這個報紙在紙上發表意見、傳遞訊息,後來呢,慢慢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網路越來越發達。
後來我再拿報紙給人家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說謝謝,因為免費。但會放下報紙,繼續滑手機,我就知道那個時代過去了。
《四方報》後來做了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6個語言的刊物。《四方報》後面資源是《立報》,《立報》的資源來自世新大學。在網路時代,紙本已經不太能養活自己。《四方報》雖然名聲在媒體圈裡面是大的,但是錢越賠越多啊,所以就收了,停刊了,我也離職了,就算失敗。
現在呢,我創辦了燦爛時光書店。當我們在說紙本被網路取代的時候,其實越慢的東西或是我們面對面的接觸,反而越來越重要。你以為在臉書上每天你有5000個朋友,每個都是好朋友嗎?才怪!大部分的人都不認識。可是在書店,你可以面對面的接觸,然後不小心撞到隔壁、可以講話,反而珍貴。

(內容編輯自2016年7月「媒體搞砸之夜」,整理:張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