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無法隱瞞真實病情 醫療處置病人自己決定

傳統法規將病人與其他關係人(包含家屬)一視同仁、擁有相同的知情、選擇與決定權;不同於此,《病主法》強調病人的自主權應具有優先性,讓家屬在參與的過程中不過度干預病人的自主性。
下文故事中的老榮民,正是因為家人隱瞞病情,造成遺憾的結果。
「癌症?我怎麼都不知道?」
老先生有陣子腹痛得厲害,太太從鄰居那裡問到偏方讓老先生服用,但疼痛並未好轉。做醫師的兒子趕緊幫父親檢查,才發現父親罹患的是胃癌,而且已經出現癌細胞轉移到肺部的「肺轉移」情況。母親一聽是絕症,認為父親受不了打擊,再三叮囑兒子別讓父親知道。
兒子不解地說:「老爸這個病會愈來愈嚴重,還會併發其他症狀,是瞞不住的。」但母親堅持不能說,幾度情緒崩潰。兒子拗不過母親,只好跟父親說胃部有個小毛病,先治療觀察再說。
老先生就在兒子陪伴下按時吃藥治療,疼痛減輕後,他嚷著不想再去醫院,但兒子堅持療程不能中斷,父子常常為此爭吵。後來疾病非但沒有好轉,老先生還聽兒子說要換其他治療方法,就跟太太抱怨兒子醫術不精,他要去找別的醫師。
太太怪他只會怨天尤人,怎不好好顧身體?「都說要多吃綠色蔬菜,你就不吃。」老先生聽了就生氣地說:「那你就別管,這是我的事!」
然而,老先生的身體愈來愈衰弱,漸漸難以行動自如,生活起居也需要太太照顧,他為此感到沮喪:「不是說一個小病,怎變成這樣了?」後來老先生住院了,沒多久就因呼吸困難被轉進加護病房。他被亮晃晃的日光燈照得刺眼,聽到四周儀器規律地發出「嘟、嘟」的聲音,還有一面百頁窗遮住了戶外的光線,讓他分不清楚是白天還是晚上。
生命一點一滴地流逝,他感到非常恐懼,用虛弱的氣音直說:「找我兒子來!」
見不到兒子和太太的身影,有好幾次他都氣得猛拍床,護理人員雖然耐心安撫他,但老先生異常激動,他們只得將他的雙手約束起來。兒子趕來,看到這幕情景嚇了一跳,斥責護理人員為什麼這麼做。這時,老先生不再激動了,他抓著兒子的手央求:「我的身體到底有什麼毛病?我不要待在這裡!」
兒子紅著眼框,深深吸一口氣,決定告訴父親:「這個病從一開始檢查就是癌症,而且已經轉移到肺還有其他地方,大概是好不了了。」
老先生聽完愣住了:「癌症?我怎麼都不知道?」他從沒想過太太跟兒子竟然一直瞞著他:「怎麼現在才告訴我!」老先生氣到無話可說,呼吸變得急促,兒子和醫護人員趕緊安撫他。
母親也走了進來,只見老先生一雙怒目,她靜默地坐在一旁,再也止不住淚水滑落。
在兒子的安排下,老先生最終住進安寧病房,整天鬱鬱寡歡,想起自己戎馬一生,多麼輝煌,如今卻只能躺在這裡等死,什麼都不能做。
「那些老戰友還沒見上一面哪,東北的老家也回不去了⋯」每當思念至此,都不禁讓他老淚縱橫,儘管安寧病房的環境舒適許多,也沒能讓老先生感到放鬆。
兒子與母親為病房做了點布置,把老先生喜歡的山水畫、相本和慣用的鐵製餐具都帶來,他們想做點什麼,讓老先生開心起來。然而,老先生終究無法諒解太太跟兒子,直到臨走前,一家人都沒能好好說出內心的話⋯⋯
家人參與疾病 不應該過度干預病人
故事結尾,讀來讓人遺憾與難過,根源則在於家人隱瞞病情,先是母親堅持這麼做,拗不過母親要求的兒子也跟著這麼做。這類故事絕非個案,它所反映的是集體社會對於病人的不信任以及醫療父權的慣性思維。傳統法規似乎也都默許這樣的戲碼不斷上演。
以醫療法來說,第63條與第64條所保障的就不是病人自主權,而是將病人與病方其他人一視同仁的病方自主權。換言之,無論知情、選擇或決定,病人均無特屬或優先的權利,病人的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有著同樣的知情、選擇與決定權。
正是在這一點上,病主法強調病人自主權應具優先性。當然,一個人生病的時候,要面對的絕不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家庭。在病情不斷發展,照護需求愈來愈複雜的過程中,病人與家人都必須不斷了解狀況並做出適當的抉擇,因此,病人自主權固然十分重要,但家人的角色也不容忽視。
家人參與疾病過程不應該過度干預而不尊重病人,病人自主也不應是任意妄為或個人主義式的自主。病人該有怎樣的自主,病方其他人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都應該在關係脈絡中去思考與建構。
病主法所規範的病人自主權基本原則,亦即病人有怎樣的知情、選擇與決定權,正是在這樣的關係脈絡中的思維成果。立法過程中,支持傳統病方自主權的聲音與希望突破現況的病人自主權主張有許多對話,交流討論的結果是正面的。
從一方面來說,病主法本身在病人知情權上面獲有重大突破,在病人選擇與決定權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如果連同「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一起來看,以病人為優先主體的病人自主權在病主法及其子法的整體法規架構中得到明確的保障。
另一方面,病方其他人在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的意義下仍有協助病人知情、選擇與決定的空間。總的來說,病主法的病人自主權是以病人為主、病方其他人為輔的規範,在病人與病方之間建立了有別於傳統醫療法規的新的關係次序。從病主法的大架構來看,以第7條為樞紐,前半部的第4條到第6條規範病人自主權的基本原則以及關係人的輔助性權利。
在任何情形下 病人都擁有知情權
病主法第4條可以說是病人自主權的根本大法,清楚規定知情、選擇與決定是病人的權利,且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換言之,當病人做了醫療上的決定且其決定是醫療方所尊重者,其他人就不得有不同意見或橫加阻礙。
病主法第4條清楚定調了「病人優先,關係人不得違反病人意願」的病人自主權架構,在這個架構上,病主法第5條與第6條進一步規範病人自主權的基本原則以及關係人輔助性的知情、選擇與決定權。在此先論病人知情、選擇與決定的自主權。
病主法規定,病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擁有知情權,不容隱瞞,沒有例外。醫療法與醫師法雖然規範醫療機構與醫師的告知義務,但告知對象並未以病人為優先,病主法則明定知情為病人權利,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告知病人為原則。醫師雖然有權利判斷告知的適當時機與方式,但無論如何都應該先告知病人,只當病人不反對時才可以告知關係人。
病人無論處在怎樣的心智狀態,醫療機構或醫師仍「應以適當方式告知本人」,依此,病人的知情權是沒有例外的。當然,病人如果不省人事或完全無法了解醫師的話,醫師就沒有非跟病人說明病情不可的義務,此時的不告知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不過,醫療機構或醫師即使面對的是「無行為能力人」或「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人時都有告知義務,其所揭示的精神是:只要病人能夠理解病情與相關醫療資訊,醫療機構或醫師就應設法在適當時機以適當方式告知病人。
病人才有特殊拒絕權 和安寧條例有差別
病主法賦予病人選擇與決定權,清楚揭示選擇與決定是病人的權利,但在進一步規範病人的這項權利時,卻依循醫療法的精神,賦予病人及其關係人一視同仁的權利,箇中原因與立法過程中的妥協有關。
病主法原始草案是以病人之選擇與決定為優先,再根據病人之行為能力與意思能力樣態,賦予關係人不同權限的輔助性選擇與決定權,不過,這個草案在立法過程中受到很大的反對而沒有通過。反對者主要著眼點為,病主法已賦予病人優先之知情權,也規定關係人不得違背病人之意願,如果同意權的部分也讓病人優先行使,他們擔心這會與醫療臨床經驗脫節而帶來太大衝擊。
雖然病主法有了這樣的妥協,但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這仍是一部以病人選擇與決定為優先的法律。首先,病主法清楚規定,對於醫師所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權的是病人,而不是關係人。其次,病主法既然已經強化了病人知情權,病人在知情之後自然就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一旦病人的想法得到醫師的認同與尊重,關係人便不得妨礙。
病主法後半段所涉及的特殊拒絕權更是只有病人才有的權利,這個規定使得病主法有別於安寧條例。安寧條例允許醫療委任代理人在其委任人無法表達意願時,代為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也允許病人最近親屬在病人沒有簽署意願書又意識昏迷的情形下,簽署同意書來代替病人親簽之意願書。
易言之,安寧條例的病人之最近親屬或醫療委任代理人,是可以代替病人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病主法則不然,病主法的關係人在非緊急狀況下固然有一般拒絕權,但在涉及生死或緊急狀況下則只有病人能透過預立醫療決定來行使特殊拒絕權,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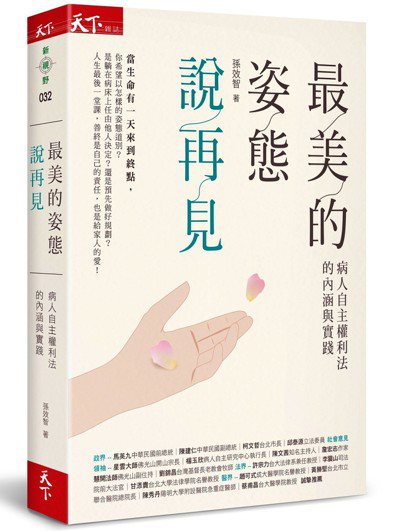
當然,在衛福部公告的預立醫療決定格式裡,病主法的意願人可以在預立醫療決定中,授權醫療委任代理人幫他決定是否要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這種空白授權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做法,可以算是間接由他人幫當事人行使特殊拒絕權的做法。
國外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後就逐漸有了特殊拒絕權的經驗,非末期病人之特殊拒絕權由旁人代理的腳步,也走得比我們快一些。
以英國《2005 年心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為例,其施行細則原本要求,病人若無預立醫療決定,則家人與醫師必須先建立共識之後請法院判決是否可以拔管,但英國最高法院2018年的最新判決免除了這個法院裁定的程序,讓他人代理拔管決定的程序更簡便。
• 本文摘自:《最美的姿態說再見: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涵與實踐》
• 出版社:天下雜誌
•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